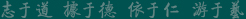作者:于亭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瞬间我竟近了知天命之年。今年(指2017年,编者注)儿子高中毕业升入大学,我忽然意识到这恰好是我考入大学三十周年。三十年前,我从边城兰州的西北师大附中,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从此,我再没有离开过校园。从边城到燕园,从朴厚的燕园来到如画的珞珈山,从一名学生成为一名教师、一介学者,读书贯穿了我迄今为止的整个生涯。说起考入大学三十周年,我忽然想起了我少年时代的读书时光。
当人对过往的人生有了某种宿命感,就会把一些事情归于因缘。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喜欢有字的纸,或许可以算作我爱读书的源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社会上凋零匮乏,物质生活,精神享受,都无从说起,西北地区闭塞贫乏尤甚,如同不毛的戈壁荒山。我虽然生长在省会城市的工程师家庭,但自小家中家无长物的情景,仍然历历在心。
我是个比较安静的孩子,不喜在外野闹,就在家里唯一的竹制小书架上翻书。家里的几十本书,除了最适合孩子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上小学的时候还读过《家庭日用大全》《赤脚医生手册》《分析化工手册》等等这种奇奇怪怪读不懂的巨册,我还读完了当时上高中的姐姐全套的中学课本,我甚至还读完了那本封面上略见油污的《大众菜谱》,觉得菜谱的世界神奇无比。后来,初中的寒暑假,禁不起母亲的恚斥,我学着给全家买菜做饭,乏人指教,我就靠这本内容朴素无比的《大众菜谱》,照本宣科,慢慢地还敢搞点儿菜式的小改良。这些经验,给了我最初的自我教育的体验。
我的父亲出生在有文化的家庭,受到过非常良好的音乐教育和基本的人文教育,热爱阅读,虽然他当年考入武汉大学,学的是化学,但一直热爱集邮、弹琴、读小说诗歌,还赋诗填词。他似乎本能地鼓励我读书聆乐的兴致。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某次他做贼一般从床底深处拖出个大纸箱,里面装满了小说,书历经年代和折腾,破破烂烂的。父亲说你读完一本再挑一本读吧,但是不许带出去。又有一次,他从里面检出一本繁体竖排的《七侠五义》,说你读读这个吧,认点儿繁体字,中国人不能不认认繁体字。于是我小学的时候,就认了无数的字和词语。这会不会是我后来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古典文献专业的一点点“因缘”,想想真觉挺有意思。
父亲时常出差,回来一定是给家里扛米,应别人家之托带的,是北京的白砂糖、花布、上海的泡泡糖和大白兔奶糖,给我的总是几本书,早先是连环画,随后就成了《红岩》《一千零一夜》《西游记》《封神演义》这种大书,甚至还有斯威布《希腊神话和传说》这种稀罕货色。小学时放学溜到同学家里玩,我也在人家四处翻书,有时候跟抄家一样。
七十年代末期的兰州,民智闭塞不开,小说和娱乐仍被视作毒草,家里有书,还得藏起来。我的好朋友是一家广东人,在他家里找到的几乎如同宝藏,是藏在天花板阁架里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等等一堆小说,还有一本三联书店50年代出版的吕振羽先生所著《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精装一厚册。
因为耽于读文史,偏尚明显,我小学的时候就开始显出偏科的迹象。记得好像是小学三年级,有过一次全校参加的成语竞赛,二百个成语填空,我居然得了唯一一个满分。而我能填对鳞次(栉)比、兄弟(阋)墙等等几个“高难度”语词,颇让老师们惊叹了一下。1981年我小学毕业,报考西北师大附中(那时候叫做甘肃师大附中),语文考了近乎满分,数学我只能得三十来分,总分勉强过线,连滚带爬,侥幸录取,进入了这个气质特异的中学,开启了我的求学之路,也开启了我真正的人生之路。
我十二岁离家住校,直到高三毕业,与三百名跟我一样全省招考进来的同学朝夕相处了六年,被一群饱学而不得志的老师们教导了六年。今年(指2017年,编者注)也是我高中毕业三十年,当我重返母校一游,宛如豪门的校园与我互不相识。我记忆中的师大附中,总是在白花花的阳光下显出难分灰黄的敝落,坑坑洼洼的操场,几十间灰瓦平房,校门内外,还箍缠交错着几条灰色的土路,散落着几栋灰色的四层楼房。目力所及,入眼的一切都是灰不拉几的。
教我们的老师,现在想起来都颇有来历,他们不少身负才学,有些原本就是大学教书匠,却贬放到中学,怀才不遇,沉郁不平,学行之中常常透出学究气和讨论探讨的气息,也偶尔在课堂上对我们这群不甚开窍的孩子流露出不耐烦。记得高中的语文课上,一口浓重的广东腔、古迂刻板的罗老师,大骂语文课本狗屁不通,说题目“诗经两首”应该是“诗经二首”,说编课本的人都是大草包,然后用了一节课给我们讲为什么得用“二”而不能是“两”,被我们这班少不更事的学生们背地里极尽嘲讽。直到我升入大学中文系学习之后,才知道他讲的是古代学问中的知识。
我们会遇到散步的老先生、教语文的康老师,他会站在路边的柳荫下跟我们谈天,话题起于我们写作文之烂,说我们手生笔拙脑子僵,而终至于说起读《资本论》。高一的时候,我终于从两三个月的餐费里抠出了五元钱,跑书店买回一套《资本论》,开始高深莫测地“读”,其实徒伤思量,连生吞活剥都谈不上。但是这种过于提前早熟的阅读,给我带来了无比神圣的感受,潜移默化之中让自己端庄矜持起来。多年之后,我才能体会到,庄重严肃的阅读,对于人生成长和成败至关重要。
青年老师会容许我们自习前后路过时,闯入他们仅容一榻一桌一架书、桌上码满了作业本的单身宿舍去闲聊,他们会与我们剧谈读书、人生和思考。高一的时候,一位据称心脏有恙不堪承担沉重教学的年轻王老师不甘无事,居然给我们开了一门选修课,叫作“鲁迅和现代文艺思潮”,一周一次课,从开课时热热闹闹到变成寥寥十余人,他一直热情高涨。当年的他,雄心勃勃,书桌的玻璃板下面压一张纸条,写着立志要做十年冷板凳,穷读精研,穷尽天下学问,揭示文学之理论真谛。听说他后来终于选择了实际的工作,去师大学生科当了个科长,也许就如此终老了。但是当年的他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经常跑到他宿舍,坐到夜里十二点半,听他讲文学、美学、文艺思潮、系统论、物理学和熵。他借给我李泽厚《美的历程》,狂读之下,我发誓要学美学,于是买了一堆美学书,朱光潜、宗白华、高尔泰、鲍姆嘉通、鲍桑葵、克莱夫·贝尔……还有黑格尔的四卷《美学》,甚至还有蔡仪的论著,凌乱无比吃力地读。我还写信给出版社邮购了李泽厚当时所有的著作,《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和《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一读之,一知半解,但如沐甘霖,如饮甘泉。我读书有个习惯,喜欢成批成系列地读,阅读某位作者的时候,也总是好大喜功,网罗他所有的作品读之。这应该是那时候培养起来的习性。
还记得高二的时候,语文老师久病难支,休了长假,校方礼请了一位老师来代了一学期的语文课,听说竟然是铁道学院的中文系主任。他时不时给我们布置不命题的作文作业,只要求诗言志而文载道,言之有物,持之有故。有一次我拼拼凑凑写了一篇七八千字的“超级”作文,题目是“何为美学”,自矜自持自鸣得意地交上去,等待他的大力称扬,结果他并没有在课堂讲评的时候表而出之,褒奖称许,让我的虚荣心好好地寥落了一番,但是他随后把我叫到教研室,认真点评了一遍,鼓励我励志读书,不要好高骛远,贪多务得。老师们的这种气质,对于那个时代僻处西北内地的省城中学来说,真是奇特无比,但我一直认为,也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和一时之会,而我恰逢其时。
我的中学,学校里有一个大的阅览室,订有好几十种杂志,还有一个小图书馆。我上高中的时候,居然开始对学生开放。下午最后两节课的时间,阅览室里挤满了学生,图书馆前排着长队。一夫当关守在门口管理外借的,是一位永远挂着厌弃漠然和公事公办神情的男老师。有趣的是,学生们往往不知道自己要读什么具体的书,图书馆也不提供书库目录让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书,排着长队的学生只能凭空描述自己需要什么类型的书。所以你每次都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结果。为此我不知道读了多少奇奇怪怪的小说,比如篇幅巨大的《金甌缺》《星星草》,还有很著名的萧军写的很不著名的《吴越春秋史话》,也让我经常意外地知道了很多闻所未闻的书和作者,全套儒勒凡尔纳的幻想小说就是从图书馆里获得,我居然还得到一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借着运动会的时候坐在人声鼎沸的操场上读完了。
为了借书有的放矢,我的午休时间几乎都耗在了书店里,先是附近十里店街上的新华书店,然后越走越远,跑到市区中心的古籍书店和规模巨大的张掖路新华书店。有兴趣的书,我得记住书名、作者、出版社,图书馆门前轮到我的时候,我就说我要某本书,竟然偶尔能找到。当我报出几本奇奇怪怪的书名的时候,那位老师脸上不免显出惊讶的表情,这使他的脸生动了许多。很多时候,他拖着跛腿钻进黑洞洞的书库,然后一头汗一身灰出来,神情烦躁,我知道他辛苦一趟,一无所获。有时候他会手里拎着一本落满灰尘的厚书出来,脸上居然一副得胜的神情。他从来没有问过我为什么要读这些书,但是终于有一次,他拉开了桌子,有点赌气地说,你自己进去找吧。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走进图书馆。两间大教室那么大,但已足以令我晕眩。那么多书,密密麻麻站在架上,延伸开去,我想,我要是能够读完,会是什么样!从此我成了常客,读书也更快,甚至图书馆不开放的时候,我可以跑到书库里去找书,帮着老师清理图书分类上架。两三年里,我们从来不知道对方姓什么,但是是他让我走进了图书馆。面对那么多书,我终于要面对抉择,我不得不自己摸索应该读什么,读哪些。也让我养成喜欢逛图书馆的习惯,一本一本、一类一类记住架子上的书。负笈哈佛的时候,我甫一安顿,就急不可耐地冲进宏大的Widerner图书馆,在宛如迷宫的书库里蹲了好几周,最终徒劳地知道,我根本没有办法穷尽它地上和地下的八层书库。
图书馆里的体验,让我生出对于书籍难以估量的情感,我会喜欢在图书馆里、在旧书店里,摩挲着那些老旧的书页,嗅着年久不散的墨香,我会喜欢结实的装帧,参差不齐的毛边书,厚实粗糙而泛黄的纸张,我期待翻开它,期待扑面而来的睿智和隽永,还有久远悠长的陈旧气息。那是一种让人愿意沉浸在里面的美妙享受。而以一个人经历之有限,图书馆中的徜徉翻览,总能给人以意外的惊喜。
中学的图书馆经历,也养成了我读书很杂的习惯,以一个中学生的好奇和不知天高地厚,面对难以计数的书籍,不是望洋兴叹,而是恨不得涸泽尽之,什么书都不管不顾地拿来读。杂读书和读杂书,向来被读书治学之士视作一忌,认为损耗精力,浮泛不专,或者目为玩物丧志。其实年深日久持之以恒地广泛读书,保持阅读的广域,不同领域的知识和思想,知见和经验,渐渐会生出条例统系,可以从中明白,知识和思想都有内在一贯的线索,也有有待阐释的例外。这种体验,借助岁月而生的阅历,时时显出触类融会的奇妙效果。少年的我,一头扎到书籍的海洋中,独学无友,显然还不懂得这些道理,但是幸运的是,那时候没有人规约我和制止我,我信马由缰,以书为友,阅读的品味在积年的深读中得到提升,渐知择别去取。我也由此有机会面对各个领域的伟大作品,辨认其中那些睿智的面孔,体味那些伟大宏阔的心灵思考的问题和提出的答案,终于广开识见,免去孤陋寡闻之病。
中学的图书馆,很快不能满足我的胃口。我开始省吃节用,更多地买书。我从读过的书的版权页上,找出出版社的邮政地址,斗胆写信,索要出版书目,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然后我挑喜欢也买得起的书,汇款邮购。省吃俭用的几元钱,花起来思前想后,久费思量,逼迫我要选出最值得买最经典的书,这些费尽周折买来的书,得之不易,我视若珍璧,也会倾全力阅读。
每次学校守门人看到我混进收发室寻寻觅觅,都会面露疑惑,因为几乎不会有学生收到信件和邮包。但逐渐他就不过来质问我了。我书架上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多数是高中的时候从商务印书馆邮购的。再就是自己逛书店,高中时期,最快乐的事情,就是中午放学午休的三个小时,我冲出教室,坐十几站的公共汽车,去市中心的古籍书店和新华书店逛,多数时间,根本就没有钱买,就隔着柜台遥望架上,请营业员拿下来看,“归而形诸梦”,不能忘怀,非要致之而后快。买书迅速成了我最大的欲望,所有的生活用度都被我降到了最低限度,省出每一分钱用来买书。空间狭小的家里堆积渐多,终于父亲找木匠打了两个大书橱,横空架在逼仄的小客厅里,而我的单人床,就架在书橱的正下面。几十年来,我买书成癖,清人袁枚说“书非借不能读也”,对我来说,一定要拥有它才能放心安心地读。我想这是匮乏年代成长起来的我们这几代人的共同心理特征吧。
曾经有一次,我看好了几种书,但绝对不可能买得起。而我许久不能割舍,终于豁出去了,壮着胆子向父亲伸手要钱。父亲问我要多少,我说一百元。他当时就沉默了,在向来慈爱的父亲面前,我从来没有如此忐忑过,像是闯了大祸。他想了半天,问我要买什么,会需要这么多钱,我一一说了,看得出他了无头绪。过了快一个小时,父亲过来偷偷地塞给我一百元,低声说:快收起来,别让你妈看见。然后他显然是松了口气,说: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不会拿钱做不该做的事情,别乱花。这笔钱,我买了《十三经注疏》、《诸子集成》、《管锥编》,还有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五大册《中国思想通史》加半套《辞源》。直到很晚,我才知道,那是身为高级工程师的父亲当时一个月的工资。父爱绵绵,如刻在心。也许他永远也不曾知道,他教会我从小热爱读书,热爱音乐,是怎样形塑了我的人生。他从来没有期待过我成功和发达,但他的鼓励,让我的人生充满了安全感,有了他的恃怙,我方能正道而行,不与时俛仰,随波逐流。
出于性情,又得到各种鼓励,从孩提时懵懵懂懂地乱翻字纸,继而饥不择食见书就读,高一的时候,因为翻读《资本论》,我记得父亲的办公室柜子里有一套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就央求他带给我。因为读其中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知道了黑格尔、费尔巴哈,很快跑去买了两卷本的《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集》乱读,又很快牵连及之,知道了费希特、谢林等等德国思想家和他们的书。读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我又知道了摩尔根和他的《古代社会》,读着读着,竟然把我慢慢地带入了人类学的园地,我开始知道有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这样的学问,又开始狼吞虎咽地搜罗阅读。
我曾经想考入大学学人类学,终于因为当时中国的大学已经彻底消灭了这个学科,这个梦想无疾而终。我从学教育学的姐姐的大学宿舍里,知道了心理学,读到了墨菲和柯瓦奇的《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也知道了荣格、弗洛依德、皮亚杰、马斯洛,还有诸如格式塔心理学、精神分析等等,还买来潘光旦先生翻译的霭理士《性心理学》。那时候尤其心醉于马斯洛的人文主义心理学,喜欢他的《动机与人格》和《人性所能达的境界》。
那时的我,就像一个掠食者,不断地搜集书籍,然后就莽莽撞撞地展开阅读,似懂非懂地沉浸在这种情境之中。眼界的不断扩大,增进了求知的热望,是我当时不知天高地厚乱读一气始料未及的结果。到了高三,我已经教会了自己有系统、有择别地找书买书和阅读好书——文学、艺术、宗教、人文、传记,还有数学之美、物理之道和宇宙奥妙,不分古今,无论中西。虽然还是不自量力地生吞活剥,但心智藉此得到培护,独立思考在心底扎下根来。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商业还没有铺天盖地,恶俗亦未昂然无忌大行于世,书店里多是比较严肃的作品,还没有像今天这样,遍是知识垃圾和无病呻吟的读物。一个西北边城的孩子,能够看到的世界,可想而知,少得可怜,但是幸而有书籍的陪伴,打开了心灵的世界,能够了解到人生和世界的无限丰富,而且从书中感受智慧,懂得高尚深沉和崇高壮美的真实性,并为之动容,沉浸不能自已,正如柏拉图那个著名的隐喻,挣脱了蒙昧阴暗和枷锁,走出洞穴,从而产生信念,追寻志趣,愿意投身智慧。
高一的时候,我开始梦想做一名学者,在大学里从事高深的学问,我想报考北京大学,因为那里有中国最大的大学图书馆。这个梦想,毫无悬念地实现了。没有什么动力,能够像热切的梦想那样,推动我在令人窒息的高中课业中快乐地学习,还挤出所有课余和自习的时间,如饥似渴地自由阅读,长想自己能够放飞梦想,展翅翱翔。高三的最后一个学期,几个老师干脆对我听之任之,任由我在他们的复习课上读些毫不相干的闲书。
我曾经想学美学、学人类学、学比较文学、学历史,最后我决定要学哲学。然而北大的哲学系根本不在西北这种不发达地区招生。最终我报考了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我觉得学不了哲学,到中文系读古书也是很棒的;第二志愿我报考了考古专业。这一选择,颇有惊悚的效果,老师们和我父亲都很困惑。
1987年,经济大潮已经席卷中国大地,“教书不如卖红薯”,教师这一行当,还没从“臭老九”的社会身份定位中翻过身来,就已在人人下海发财和读书致富论的浪潮中打入泥沙,直接沉底,校长和老师都很负责任语重心长地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高考无忧,却不报考北大的招生目录中唯一看着还像样的经济法专业。父亲则忧心忡忡地说:你花钱买书不眨眼,将来读中文当老师,既贫且贱,还不得穷死?难道我还能养你一辈子?并且他列举自己毕业时武汉大学要他留校任教幸而没有服从为例,历数同学中留校的都没有好日子好下场,来劝说我学点不那么玄虚缥缈的东西。从他们的劝说中,我觉得我未来准定是潦倒无着,贫寒而无立锥之地了。不过我不为所动,因为我热爱我的梦想,热爱沉浸在思辨和人文学术中。看到我的坚持,父亲说:你真的想好了?想好了就去做吧。四年后当我报考了研究生,他又同样劝说我早日工作,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而最终又同样如此鼓励了我。
多年之后,当我面对儿子,看到他从产生梦想,到申请大学,其间他数次与我们商量取舍去从,我总是想起父亲对年少的我的一路鼓励和不遗余力的呵护。面对孩子的选择,我也会感到无助,心里没底,但我终于能对孩子说:儿子,如果你想好了,愿意面对一切艰辛,就去试试吧!我的孩子冲刺他的最高目标的时候,承受了压力,应对了挑战,展示出了他最为美好的才性,实现了我想都没有想过的梦想,远远地超过了当年的我。事后他才告诉我,他很早就想去那所学校,步入拱廊,走上那条宽大的楼梯,坐在他魂牵梦绕的古老拱顶下读书。他做到了,因为他也是一个从小热爱阅读的孩子。当我身为人父,看着挺拔自信的儿子,为他感到骄傲的时候,我想,父亲一定也视我为骄傲。
造就这一切的,是出于趣味、不含功利目的、不追逐外在成功、全力朝向文化的阅读,这种阅读早熟而严肃,挑战心智,因了内在的热情而持续不辍,它难以估量地提升了人生的品质,我和我的孩子从中获益终身。
正如康德论断“什么是启蒙”所说的:“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我招致的不成熟。”阅读对于心智的开启,从我的感受来说,效果无限惊奇。我在稚嫩好奇、叛逆善感的青春期,开始知悉黑格尔所说的“人应该尊重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这一道理,并产生持久的共鸣。
读书促成了我的梦想,让它成形,然后得以实现。读书更让我免于怀特海所说的僵化陈腐的教育中“呆滞的思想”之毒害,让我一生朝向文化,朝向对美和高尚情感的接受,而不再以“有用”和“一技傍身”的职场知识为目标。读书终于成为我一生的志业,而当我终于成为一名从事高深学问的学者,读书显然意味着更多。它成为日常不可或缺的存在,无论我走到哪里,随身总是习惯性地带着几本书,家中枕边厕中,触手可及都放着书,可以随时拿起,随时开卷展读。而书籍对于我从来都不是工具和用品,它们是相伴相随的朋友。我舍不得令他们污折尘染,受到冷落和委屈。韩愈诗称李泌家富藏书,“插架三万轴”,而“新若手未触”,司马光说自己读书惜书,“必先视几案洁净,藉以茵褥,然后端坐看之”云云,都是爱书之语。没有年深日久的相随相契,是很难产生这种情感的。我周围的一些学生和同事,他们没有一支跟了自己多年的钢笔,经他们读过的书本,则污损敝破,形同遭劫,这是我一直难以理解的。
现在想想,从小学到中学,读书若渴,但也自不量力。可是从我和我的儿子的经历来说,一个孩子,其实心智的潜力惊人,特别容易从书籍和艺术中感知高尚壮美,获得一种饱含崇高悲悯之情的悲壮感。孩子也比我们料想的更加具有理解力,虽然他们清浅稚嫩,知识不足,阅历不足,但是严肃深沉和强劲的书籍,特别容易感染单纯的心灵,令其受到感召而生上进之心,也培养出他们诚挚深厚、富含同情的情感方式。作为教师,我时时痛感现在一茬一茬的孩子,越来越放弃挑战心智的阅读,面对阅读他们缺乏基本的耐心,从而变得感知迟钝,封闭乏味,目光短浅,粗糙浅俗甚至鄙陋无文。
回首往事,清苦枯燥的中学时代可算是我读书生涯中最好最美的时光,而大学及其后,不过是其顺理成章的延续和开展。审视自己年少之读书,开始如盲人摸象,而年少轻狂,弯路不少,个中滋味甘苦,感受之切,使得我特别能与怀特海所言“自我发展才是有价值的智力发展”一语发生极深极大的共鸣。而陈寅恪先生尝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尤其于我心有戚戚焉。“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才是读书真实的意义。(作者系文学院副院长、国学院副院长、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