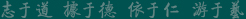作者:秦申,武汉大学国学院2015届本科毕业生。现为教育工作者。

今年正逢国学院成立十周年,脑海中不期然跳出来的,却是林逋的这句“不须檀板共金樽”。仔细想想,这句诗恰可概括我在国学院所学到的最宝贵的东西——对国学的兴味。
进国学班的时候,抱着单纯而乐观的“经世致用”理想。日日读四书,读到子曾经曰过:“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很赞叹,很欢喜,觉得自己也要像颜回一样,安贫乐道,自得其乐,不管窗外的雨横风狂。 但子又曰:“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夫子尚且心心念念,要做出一番事业,于是自己也受了十分的勉励,想要去风雨中闯荡一番,建功立业。 初进国学院,日子在这种向往和矛盾思索中热热闹闹地流过。
国学弘毅班与众不同,正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不可等闲视之,故此院里专门请来文史哲三院的博士生导师,来给我们这些本科生讲课。 历史学院的谢贵安教授,讲“史学方法论”,课堂在狮子山的山顶。每次上课,师生都要先从樱花大道,沿着台阶,一路爬到山顶,再进一幢三层小楼。待到坐定,众人额上已有微汗,体弱者则吁吁气喘。教授曾戏称:“讲这门课,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
九月开课,先讲“历史是什么”,唬得大家由史入哲,暑热未尽的时候,钻到图书馆去翻大部头。十一月讲到“年鉴学派”和“实证主义”,讲兰克如何秉笔直书,这时狮子山上的叶子已红了,片片铺在台阶上,伴着一阵冷雨,是另一种凄美的景致。
到一月份,临近寒假,课程内容讲完了,教授又讲起做学问时的一些掌故:段玉裁如何校订《说文解字》,把"牙,牡齿也”改成“牙,壮齿也”;农民如何伪造文物,又如何自作聪明地在铁剑上刻“闯王李自成之剑”。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 那一年的冬天很冷,有一次课前,下了一点薄雪,天寒地冻,路滑难行,但这阻不了我们听故事的勃勃兴致。下了课,天已黑透,先去老斋舍里面的小店,买一碗热腾腾的麻辣烫。端着碗,一路吃,一路聊,一路往回走。后来老斋舍整修,麻辣烫小店就转到了湖滨宿舍区,可是再去吃时,一样的店主,一样的食材,却再也没有那一年的味道了。
历史课之外,国学院还开了经学课。之前的国学教育,读“通论”,读“简史”,学生学了四年,说起来滔滔不绝,细究之下,原文一概不知,观点拾人牙慧。鉴于此,国学院先教大家读四书,读五经,从原文着手。秦平老师讲《论语》,风度翩翩;刘乐恒老师讲《孟子》,带着真切的体悟;骆瑞鹤老师讲《荀子》,考证精严。这三门课,让我受益匪浅。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任慧峰老师的“经学通论”课。 这门课是春天开始讲的。一般来说,武大的春天,春风熏熏然,吹开樱花,是最美的时节。
然而那一年的春天,连着下了一个多月的雨,到了四月中旬,樱花还没完全绽放。每逢周四,经学通论上课的那天,必是春雨绵绵,天气阴冷。踩着水湿淋淋地到教学楼,走廊上摆满了五颜六色的雨伞。进教室白炽灯也白惨惨的。等大家把皮锡瑞那本文言写成的《经学历史》摆好,任老师就开始讲课。
任老师说话,一向轻言细语,讲到精微处,声音越来越小,闭着眼睛,皱着眉,一边踱步,一边思索,就停住了。我那时,对经学半懂不懂。课本既是文言,老师又常沉浸在经学世界中不可自拔,于是对这门课,便只记得下雨、冷、和一大堆名词,例如什么“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家法”,“京房易”之类,还有为学问争来争去的清代人。后来自己努力读了很多“子”书,又精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学识渐长,才慢慢品出这门课的好处。好课正如好茶,一点苦涩,三分回甘,愈品愈悠长。
其实任老师最擅长的是经学中礼学部分。后来我跟着他研读“三礼”,在珞珈山上的小楼里上课。众人围坐,读流水簿子一样的《仪礼》、《周礼》。他细细地给我们讲古人的衣帽形制,古人的婚丧礼仪,古人的站位座次,对于疑难的地方,绝不蒙混过关。每读一节,就去博物馆找实物对照着看,收获颇丰。任老师常说:“礼,好学难治。”他以研究礼学为终身志向,这是一条冷清而艰辛的路。我曾看到他在人来人往的办证大厅,旁若无人,手不释卷。“回也不改其乐”,大概就是任老师这样了。但任老师也很随和,和同学们一起玩狼人杀,聊电视综艺,眉飞色舞。说起家里的地板被水泡坏了,孩子要上学,也是一样的烦恼。我钦佩他的品格。这种治学为人的真诚和专注,是真正的言传身教。
升到了大三大四,学的内容深了,反而开始怀疑起自己是否能“为万世开太平”来。天天“之乎者也”,真的能经世致用吗?还是说,我们学的,是泡在福尔马林里的文字,最多只能进图书馆、博物馆,供人参观?
每当我们在课堂上蔫蔫的,或是有同学灰心丧气,于亭老师就给我们鼓劲。于老师是国学院的副院长,国学班是他的心血,国学班的每个同学,都是他的孩子。于老师其人,能“舌灿莲花”。平时精致、讲究,听古典音乐,用lamy钢笔,写一手漂亮的瘦金体字,连照片都是回眸一望,潇洒出众。谁能想到这么一个“华丽”的人,会殷殷切切地嘱咐呢?但看到我们泄气,他就忍不住唠叨,给我们讲他当年在北大求学,如何饿得靠喝水充饥,在武大教书,又如何用盆来接家里漏进来的雨。于老师极会渲染气氛,一件平平无奇的事也能讲得跌宕起伏。一听他讲故事,下面坐着的,个个都来精神了。
有时候讲了故事,大家还是泄气,于老师也忍不住学我们没精打采的样子,深叹一口气。我有一张李诺烺学姐画的画像,颇有于老师叹气时的神韵。珍藏多年,现在拿出来,国学班的各位看了,大概会会心一笑。
叹过气后,他还是会鼓励我们,以能灿莲花之舌,继续把课上得姹紫嫣红,中文与English齐飞,文言共sinology一色。 本科毕业后,我告别国学院,升入古籍所读研,研习一些更切实的考据学问,对国学院,仍深有眷恋。想起国学院的同学们,去泰山,在山上用粤语吟诵《望岳》;去敦煌,在火车上谈诗词,在沙漠中观星……想起国学院的老师,余婉卉老师一丝不苟的可爱,刘乐恒老师的以茶会友……想起国学院开设的种种课程,纯英文的” The Republic”、 ” The Confessions”、 ”Bible”研读,文言的四书五经,所有的这一切,熏陶出的,是一种对文化纯粹的兴味。
现在我已入社会,不再去想“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了,反而离“士不可以不弘毅”的理想,更近了一些。
曾是珞珈山上一书生。现在,虽不在珞珈山,但在国学院所耳濡目染的一切,仍然紧紧地跟着我。国学院十周年,让我们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载歌载行。
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于知春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