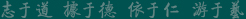受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教授之邀,近期台湾明道大学张丽珠教授来我校讲学。张教授分别于12月16日、18日和22日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大报告厅举办了题为《明清思想典范转移与清代新义理学》、《衔接传统与现代的清代新义理学》与《我的< 中国哲学史三十讲>书写、英译与台湾其他哲学史书写比较》的三场学术报告。三场讲座分别由吴根友教授、郭齐勇教授和丁四新教授主持。
张丽珠教授早年毕业于台湾国立高雄师范大学国文系,之前任教于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国文系,现为台湾明道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其代表作有《全祖望之史学》和被誉为“清代新义理学三书”的《清代义理学新貌》、《清代新义理学——传统与现代的交汇》、《清代的义理学转型》以及有繁、简体和英译本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三十讲》。其关于清学研究的汇总之作——约100万字的《清代学术思想史》也预计于2016年出版。
在讲座伊始,张教授总结了以往学术界对清代思想的主流看法。首先,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不承认清代思想有高度可言的普遍性看法。其次,钱穆在其与梁氏同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尽管承认清代有所谓的义理之学,但不过是宋明理学的蜕变和余波,并无甚可称道的高明之处。最后,她特别强调了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港台新儒家根本否认清代存在思想,牟氏在其广为流传的中国哲学入门教材——《中国哲学十九讲》的结尾处说到:“我们这个课程只讲到这里,明亡以后,经过乾嘉年间,一直到民国以来的思潮,处处令人丧气,因为中国哲学早已消亡。”因而以往的哲学史教材,讲到清代哲学的时候,就只谈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最多再论述一下颜元和戴震,就不会往下展开了。
张教授在检讨了以往的学术史后,展开了自己对清代新义理学的认识。首先,她明确区分了“学术典范”与“思想典范”两种不同类型。两者有时是合二为一的,有时是分而为二的。譬如宋代的理学,既是当时学术研究的典范,如程颐的《周易程氏传》、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同时也是其思想义理的典范,如濂、洛、关、闽的心、性、理、气之说。而以往我们所强调的乾嘉考据学,则只是清代的“学术典范”,而非其“思想典范”。如果我们只看到其考据的形而下的“器”的层面,而忽略了其义理的形而上的“道”的追求,则自然会质疑清代有何思想?所谓清代的“思想典范”乃是基于清儒所特长的考据方法论所建构的革新之前理学的形上模式者,即戴震所倡导的“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乾嘉新义理学,并且为焦循、阮元、淩廷堪等徽州及部分扬州学人所继承。所以胡适称他们都是“以精密的考据方法来包装哲学主张”,都是“从经学走上哲学路上去”的学者。而清初的理学名家,尽管其不失为理学的蜕变性发展,但却不是根基于清人所特长的考据方法论,故而无法彰显清人的思想特色,因此不能看作为清代思想的典范代表。所以,由宋到清,其学术典范是由理学转向考据学,而其思想典范则是由理学转向新义理学。
关于清代是如何转向考据学的,张教授也有一番自己的独特观察。她纠正了以往学界刻意强调清代文字狱的政治因素,特别强调我们应该从学术自身的发展演变上去找原因。她认为,清初非但不打压学术,相反却是鼓励讲学。康熙服膺朱子理学,极为重视经筵讲学,自称“读书五十载,只认得朱子一生居心行事”,甚至欲升朱熹“跻位四配之次”,经过李光地的劝谏阻止,乃“定列祀于十哲之末”。而民间讲学之风,更是昌盛:北学孙奇逢、南学黄宗羲、关学李颙,当时并称为“清初三大儒”。考据学的兴起不是源于政府的打压,而是来自于清初的群经辨伪学,即清初理学家内部的“朱王之争”。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批评朱子学者信奉“陈抟而歧入道家”,“过视象数以为绝学,故为其所欺”。陈确的《大学辨》,则是接续王阳明与刘宗周的遗业,批评程朱一系篡改和误解《大学》古本,而他所做的工作则是“欲还《学》、《庸》于戴《记》,删性理之支言,琢磨程朱,光复孔孟”。而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则是朱子学者对阳明学者所奉为经典的“尧、舜、禹之相授受”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论学根基之批判。经过群经辨伪之后,理学奉为圭臬的《易》图、《大学》、《古文尚书》被证为伪作,理学也因失去了经典权威的支撑而被撼动根基。既然以前所信奉的精神偶像被彻底打倒了,那么唯一可以信而无疑的则只有考据本身了。由此,考据学也逐渐从最初的辅助性的辨伪工具,一跃而成为主流学术的评价标尺和研究对象。而这才是由理学转向考据学的最具体而直接的学术原因。“水盈科而后进”,学问亦复如是。譬如诗有唐宋之分,唐人写诗重意象之描摹,宋人写诗重境界之表达,所以钱锺书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此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也。在义理学方面,也是如此:宋儒的焦点在于“性善如何可能”的形上层面的“证体”,而清人则侧重于“善如何去落实”的形下层面的“实践”。其实学术课题本身也是时代课题的反映,当时社会存在着严重的道德“伪善”和“以理杀人”的伦理异化现象,清人尝试去建立一个合乎人情的道德标准,强调“趋利故义”,两不相妨。并且与宋儒所主张的“德性之知,不假见闻”不同,清人特别强调“德性资于学问”,“能知故善”、“唯智能生万理”。由此,将考据方法论与其新义理思想结合起来,重新解读和建构了儒家经典诠释系统。
张教授特别指出,其所揭示的清代新义理学,并不仅仅限于乾嘉时期,而是贯穿整个清代历史。首先,从宋明理学到明清气学的转变,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明代中叶以来,便有很多“气本论”的哲学家,他们逐步转向“形下者谓之器”的“实在界”论域来展开其思想命题,如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黄宗羲、陈确、颜元等人。陈确说:“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颜元说:“正其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他们批评了“贵义贱利”、“求利害道”的传统观念,开启了“尊情尚智”、“达情遂欲”的思维方式。而这种迥异于理学传统的“存理灭欲”的价值观念,在戴震、焦循、阮元、淩廷堪等人那里进一步系统化和条理化,之后为清末民初思想家严复、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所继承,并做了一个中西思想文化传统的嫁接和转化。
所以,清代新义理学的价值在于,它一反宋儒“义利二分”的“存理灭欲”的思想传统,开创了“义利合一”的“达情遂欲”的新伦理观,它突出了儒学的客观化途径,实现了儒家义理的全幅开发,这既是儒学现代化的本土资源,也有利于弥补“西学外铄说”之不足。张教授特别指出,回顾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文化长河,明清之际实为传统与现代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儒家哲学是一种强调形而上的道论层面的先验取向;在此之后,则是一种重视形而下的器物层面的经验取向,这是中国儒学“自转化”的一大关键点。概而言之,清代新义理学是连接中古哲学与现代性思维的一个过渡桥梁。由此,我们可以把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所受到的西方文化冲击影响的最初阶段,提早到在其200年之前的明清之际的本土价值观念转换时期。而近代以后,这两股本土与外来的思潮汇流,则加速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以往的哲学史研究,既没有看到清代思想的独特性(即其与之前古典哲学的不同之处),也没有发现清代思想的连续性(即其对现代性思维的过渡作用),这是一个亟待纠正的学术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在细致阅读文本的基础上,全面看待中国哲学史上的各家学派,而非厚此薄彼,甚至略而不论。
正是基于对清代新义理学的多年研究心得,张教授后来撰写了《中国哲学史三十讲》一书,把之前陷入低音的思想家,都给予了应有的正面评价。她在书中特别批评了新儒家当道的台湾学术界,在中国哲学史的书写立场上,过于强调儒家哲学的道德形上学一面,因而存在着两大严重的偏失之处:第一,对墨家、法家的评价未尽公允;第二,对汉儒、清儒之强调“气性论”者的评价未尽公允。此外,该书还吸收了出土文献方面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补充了孔孟之间的儒家早期性命思想和作为政治哲学的汉初黄老道家思想。后来该书还曾荣获台湾前国立编译局“全国重要学术著作英译出版奖励”,成为继冯友兰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之后的又一汉著英译的哲学史著作,促进了英语学术界对当前中国学术动态的了解。
在各场讲座提问环节中,张丽珠教授就同学们关于其与余英时、沟口雄三等学者的观点异同、清代新义理学与宋明理学之间的发展衍变等提问,都给予了细致详实的回答,取得了良好的互动效果。张教授饱含深情的演说方式、温文尔雅的古典气质、充满睿智的学术思考,给广大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吴根友院长所点评的那样:“张教授,不仅学问做得好,而且课也讲得好,堪称‘巾帼不让须眉’,我们听后都获益匪浅!”
韩书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