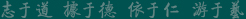也谈“亲亲相隐”的法律实质、法理依据及其人性论根基
——兼评邓晓芒教授的《儒家伦理新批判》
刘水静
内容提要:儒家传统思想中的“亲亲相隐”理论之正当性问题,是近年来国内哲学界争论不休的一个热点话题。在《儒家伦理新批判》一书中,邓晓芒教授从“隐私权”的角度界定和阐释了现代西方亲属容隐制的法律实质和法理依据;在此基础上,邓老师对中国儒家传统中的“亲亲相隐”思想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其实,邓老师的这些观点都是值得重新讨论和商榷的:西方现代亲属容隐制度所体现的不是一项“隐私权”,而是一项法律“豁免权”;其法理依据是“期待可能性”理论;其人性论根基是我们自然天性中的“亲亲之爱”。
关 键 词:亲亲相隐 容隐制 隐私权 期待可能性 爱有差等
2007年初,《学海》杂志刊发了邓晓芒教授的长文《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国内学术界围绕儒家“亲亲相隐”这一主题所爆发的第二轮大辩论由此拉开序幕。三年之后,邓老师将其在此次论战中所公开发表的系列文章结集成《儒家伦理新批判》一书,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恰如邓老师所言,此次论战的主题之一,就是“亲亲相隐与西方法律容隐制度的关系问题”。在《儒家伦理新批判》一书中,邓老师立足于“西方现代法制国家”所建立起来的“先进完备”的“容隐制度”,对中国古代法律传统中的容隐制与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亲亲相隐”观展开了严厉的鞭挞。然而,深入考察邓老师的相关阐述,我们将会发现,邓老师对西方现代法律规范中的亲属容隐制的法律实质、法理依据及其人性论根基的理解,存在诸多可商榷的问题。因此,如何理解中西文化传统中的“亲亲相隐”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评价儒家“亲亲相隐”思想资源的当代意义,就成为了有待继续深入交流的话题。本文即从西方现代亲属容隐制的法律实质、法理依据及其人性论根基的角度,尝试与邓老师展开对话,以图将问题的理解真正引向深入。
一、论从个人“隐私权”的角度理解西方亲属容隐制的做法是否恰当
在相关讨论中,邓老师反复强调,西方现代法律中的亲属“容隐条款”是一项“权利条款”1,这种“容隐制度”究其实质是“把亲亲互隐当做一项人权即个人‘隐私权’纳入了现代法律体系”。2在更进一步的论述中,邓老师甚至从“隐私权”的角度对“亲属容隐权利”的“法理根据”作了界定:“孟德斯鸠所表述的只不过是近代容隐制的法理根据,即剥夺人的隐私权是不人道的、罪恶的。”3在本文看来,从“权利”的角度理解西方现代法律规范中的容隐制度是对的;但是,从个人“隐私权”的角度来阐释这种“权利”的法律实质及其“法理根据”的做法却是值得商讨的。为了弄清楚这一问题,我们先从当代西方两大法系中的容隐制度之区别开始谈起。
概言之,当代大陆法系中的亲属容隐制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1),为使犯人免受处罚,犯人的亲属拥有“拒绝作证”4和“知情不举”5的权利(我们可以将这种权利称为亲属容隐制中“消极的”或“不作为”的权利);(2),为使犯人免受处罚,犯人的亲属可以“藏匿”、“包庇”犯人或主动帮助犯人毁灭、转移罪证而不受或可以不受处罚(我们可以将这些内容称为亲属容隐制中的“积极的”或“主动作为”的权利)。6
与大陆法系中的亲属容隐制相比,当代英美法系中的亲属容隐制内容较为单薄。首先,英美刑法在规定“帮助罪犯罪”和“妨碍审判罪”时均强调,“任何人”——包括犯人亲属在内——“藏匿”、“包庇”犯人时“都会构成犯罪”。7其次,当代英美法系将“知情不举”也排除在亲属容隐制的范围之外了。英美刑法中的“知情不举”分两种情况:其一是,“任何人”以获取犯罪人的“报酬”为条件,而不举报该项犯罪行为的,均以“隐瞒罪”论;其二是,“任何人”在没有接受报酬的情况下不举报犯罪行为的,均不构成犯罪。也就是说,“知情不举”的情况是否合法,不取决于行为主体与犯罪人之间是否具有“亲属”关系,而仅取决于行为主体是否获得犯罪人的“封口费”。8最后,在排除了犯人亲属可以“藏匿”、“包庇”犯人或主动帮助犯人毁灭、隐藏罪证而不受处罚的条款及“知情不举”的条款后,当代英美法系中的亲属容隐制的内容主要限定在亲属“拒绝作证”的权利之上,而且拥有该项权利的“亲属”也只限于当事人的配偶。9
弄清当代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之间的上述差异之后,我们再来看当代西方主流隐私权理论是如何界定“隐私”和“隐私权”之具体内涵的。国内学者张莉在《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一书中恰当地指出:“隐私权是一个处于发展中的权利,其概念尚未明晰,未取得一致的见解。”10美国学者托克音顿亦说:“美国学术界对隐私的定义五花八门。”11全面清理和归纳关于隐私和隐私权的这些“五花八门”的定义,显然不是本文的主题。本文围绕隐私权这一概念主要讨论的问题是:在现代西方国家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中,亲属容隐制与个人“隐私权”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是否可以如邓老师那样从“隐私权”的角度理解容隐制的法定内涵及其“法理根据”。
我们先看在美国立法界和司法界中较为常见的关于隐私权的定义,这一定义体现的即是当代西方隐私权理论中最为流行的“个人信息控制权理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美国司法部诉记者联盟案”的判决中指出:“无论是从普通法还是从字面上来理解隐私权的内涵,[隐私权]都强调的是个人对有关自己资讯的控制。”12美国克林顿政府也将“隐私权”界定为“个人控制在什么条件下收集、披露和使用个人信息的权利”。13显然,从“个人信息控制权”的角度所界定的“隐私权”概念,或许只能够解释现代西方亲属容隐制中所规定的“消极的”或“不作为的”权利,即犯人亲属的“知情不举”和“拒绝作证”的权利。也就是说,根据“个人信息控制权”,个体公民有权利自行决定是否将其所知悉的有罪亲属的犯罪情节或相关罪证上报司法机关或是否出庭指证其有罪亲属。14斯特龙所主编的解析英美证据法理论的经典著作《麦考密克论证据》一书15即谈到了从“隐私权”的角度诠释亲属“拒绝作证”之特权的可行性。16但是这种从“个人信息控制权”的角度所理解的“隐私权”显然不能被用来解释亲属容隐制中所规定的那些“积极的”、“主动作为的”权利,即上文所述的主动“藏匿”有罪亲属、为其“湮灭罪证”等行为的不受或可以不受处罚的豁免权。因为公民有权自主决定是否向他人透露其个人“资讯”或“信息”与公民有权为其有罪亲属“提供住所、隐蔽场所、生活费、生活手段或其他任何逃避侦查、逮捕之手段”17、甚至为其“毁灭、改变或者移动对于刑事调查具有重要意义之物品、或者消除犯罪痕迹”18是两码事。19
除了“个人信息控制权理论”外,当代西方隐私权理论的另一较为流行的定义是“独处权说”。与“个人信息控制权理论”强调“个人信息”方面的隐私不同,“独处权说”强调个人对“私人行为”和“私人活动”的不受外界干预的自主决定权。如道格拉斯法官所指出的,隐私权“包括个人有权规划自己的事务,每位公民有权不受干扰地以自己认为最佳的方式规划自己的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去自己想去的地方”。20现行德国宪法也从“保护人类尊严与人格的发展”的视角强调了个人对其“私人行为”和“私人活动”的独自决定权。21那么,我们能否从“独处权说”这一理论视角来解释西方亲属容隐制中关于藏匿有罪亲属和湮灭犯罪证据等行为的法理依据呢?要想搞清楚这一问题,我们需要首先弄明白“独处权说”为个人“隐私权”所设定的边界。
其实,当“独处权说”捍卫个人的对其“私人行为”所具有的不受干预的自主决定权时,它本身就要求我们首先对“私人领域”或“自决隐私领域”与“公共领域”作出明确的区分。也就是说,当我们的行为越出“个人的私密空间”从而对他人形成某种影响甚至损害时,我们就不再能够援引个人的法定“独处权”来谴责他人或法律对我们这种行为的干预及制止了。所以,托克音顿指出:“美国的刑事和民事法律规则反映了这样一种普遍的思想:自决当中的伤害、重大过失行为应当被禁止。这一认识与密尔的观点是一致的:‘自决隐私’是指‘自决行为’的范围,而这种‘自决’行为不能对他人造成伤害。”22
在此基础上反观亲属容隐制中所规定的藏匿有罪亲属和湮灭犯罪证据等行为,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根本就不能将容隐制中的这些行为归入“自决的隐私领域”之中。因为,犯人亲属的这些举动明显越出了所谓的“私人领域”,而且这些行为本身就已经对国家的司法职能之行使造成了某种干扰甚至阻碍。所以当代西方大陆法系国家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对“隐私权”和亲属容隐权作出了非常明确的区分:“隐私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其他任何个体、甚至国家和法律本身都不能阻碍主体对该项权利的合法行使;而公民的“隐亲”权,仅仅意味着公民庇护和藏匿其有罪亲属时享有法律所规定的“免于处罚”或“可以免于处罚”的豁免权。23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理解这种“豁免权”与个人“隐私权”之间的区别:A基于其法定“隐私权”而实施某一行为,在此过程中,法律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不能干涉或制止这一行为,同时法律也不允许其他人干涉或制止这一行为;而B为了使其有罪亲属C逃脱法律的惩罚而庇护、藏匿C或毁灭、转移C的犯罪证据而被发现时,法定的容隐制度显然不能保障B的藏匿行为不被法律(或司法人员)干涉或制止,而只能保障B这种行为免受或可以免受处罚。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邓老师从当代西方关于隐私权的主流理论的角度出发界定亲属容隐制的“法律实质”和“法理根据”的做法是不恰当的。考察《儒家伦理新批判》一书,我们可以发现,邓老师是在对儒家“亲亲互隐”所展开的第二轮批判——即《就“亲亲互隐”问题答四儒生》一文——中首次从“隐私权”的角度诠释西方现代容隐制的。在此文中,邓老师就陈乔见先生在《逻辑、理性与反讽》一文中所谈论的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有关“容隐制”的两段文字分析道:“其实,孟德斯鸠所表述的只不过是近代容隐制的法理根据,即剥夺人的隐私权是不人道的、罪恶的。”事实果然如此吗?让我们仔细读一遍孟德斯鸠的这两个例子吧:
勃艮第王贡德鲍规定,盗窃者的妻或子,如果不揭发这个盗窃罪行,就降为奴隶。这项法律是违反人性的。妻子怎能告发她的丈夫呢?儿子怎能告发他的父亲呢?为了要对一种罪恶的行为进行报复,法律竟规定出一种更为罪恶的行为。
列赛逊突斯的法律准许与人通奸的妻子的子女或是她的丈夫的子女控告她,并对家中的奴隶进行拷问。这真是一项罪恶的法律。它为了保存风纪,反而破坏人性,而人性却是风纪的泉源。24
在这里,孟德斯鸠的表述再清楚不过:列赛逊突斯的法律“准许”(“permits”25)亲属之间的互相“控告”,而孟德斯鸠则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真是一项罪恶的法律。”显然,在这个例子中,孟德斯鸠认为好的法律不应“准许”亲属间的互相“控告”。“如果”说孟德斯鸠通过勃艮第王贡德鲍的例子,指出亲属间应具有“相隐”的权利,即亲属相隐是“正当”的话;那么他通过列赛逊突斯的法律的例子则指出,亲属间应具有“相隐”的义务,即亲属相隐是“应当”的。邓老师全文照引了孟德斯鸠的这两段话,却未能仔细读完它们,就想当然地从西方现代容隐制的一般原理出发,将孟德斯鸠的亲属容隐观完全解释成一种“权利”,这一做法着实轻率。
比如,在接下来的论述中为了强调孟德斯鸠的容隐观所体现的是一种“权利”观念,邓老师再一次拉出“中国古代法律”中的亲属容隐制度来作反衬,并指出,“不准许与人通奸的妻子的子女或是她的丈夫的子女控告她”的法律,即是“把亲亲相隐当作一般人际关系中的一项‘义务’”,这种代表“中国古代法律的情况”的做法“同样是违反人性的”。26果真如此的话,孟德斯鸠的亲属容隐观也就“同样是违反人性的”了,因为他在列赛逊突斯的例子中所强调的观点就是亲属相隐是一项“应当”为之的“义务”。再如,在稍后的分析中,27邓老师引出古希腊著名悲剧《俄瑞斯特》的例子并指出,该例子揭示了家庭成员“有按照法律关系揭发亲属罪行的权利”,而这与孟德斯鸠的例子是“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的。28“如果”《俄瑞斯特》的例子确实宣示了亲属相互告发的“权利”的话,那么这一例子就与孟德斯鸠所强调的亲属容隐的“义务”直接相抵牾了,而不是什么可以“并行不悖”的。
最后,邓老师关于“孟德斯鸠所表述的只不过是近代容隐制的法理根据,即剥夺人的隐私权是不人道的、罪恶的,这一点,不论是在我的还是刘清平的文章中都丝毫也没有否认”的说法同样难以成立。因为第一,正如本文已经指出的,从“隐私权”的角度理解西方近代容隐制的法理依据的做法本身就是不适当的;第二,从孟德斯鸠的“表述”中,我们不仅不能得出“剥夺人的隐私权是不人道的、罪恶的”这一观点,反而能够得出“废除亲属容隐义务的法律是‘不人道的、罪恶的’”这一与邓老师直接相抵牾的观点;第三,通读《儒家伦理争鸣集》一书所收录的刘清平先生的六篇批判性文章,我们“丝毫”找不到其关于“近代容隐制”与“隐私权”之关系的的只字论述,“隐私”一词甚至根本就没有在刘文中出现过。所以,与其说刘清平先生“丝毫”没有否认邓老师的“这一点”,不如说他从未“丝毫”肯定过“这一点”。
现在我们可以对关于“隐私权”与“西方现代容隐制”之关系的讨论作个总结了。在本文看来,邓老师从“隐私权”的角度讨论“西方现代容隐制”的“法理根据”的做法不但是建立在其对孟德斯鸠的相关文本的误读基础之上的,而且也难以从现当代西方国家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中获得有力的确证。那么,现代西方亲属容隐制的立法根据(或“法理依据”)究竟是什么呢?
二、从“期待可能性理论”的角度谈当代西方亲属容隐制的立法根据
“期待可能性理论”之起源的直接契机是1897年德意志帝国法院的“癖马案”判例。29该理论几经发展,于19世纪20年代在德国成为通说,随后被介绍至日本,在战后日本亦获得通说的地位。2008年4月,由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承办的“第五届全国中青年刑法学者专题研讨会暨‘期待可能性’高级论坛”的召开,则显示了“中国学者对于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期待非常之高。”30
所谓期待可能性,亦称“适法行为的可能性”31,是指在行为人所处的具体情况下,有能够期待行为人不实施违法行为而实施其它适法(合法)行为的可能性,反之,则为“期待不可能”或“无期待可能性”。正如日本刑法学家大塚仁教授与大谷实教授所指出的:“为了能够说行为人存在责任,除了行为人具备责任能力、责任故意或责任过失外,进而还需要行为人存在实施适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32而“在[犯罪]行为人没有期待可能性的时候,即便其对犯罪事实具有认识,也具有违法性意识的可能性,但也不承担故意责任或过失责任。”33
在中日法学界,期待可能性理论被广泛运用于当代西方大陆法系中之“亲属容隐制”的法理解释之中。比如,《日本刑法典》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犯人或者脱逃人的亲属,为了犯人或者脱逃人的利益而犯前两条之罪(即《日本刑法典》第一百零三条所规定的“藏匿犯人罪”和第一百零四条所规定的“隐灭证据罪”——引者注)的,可以免除刑罚。”34对此,大谷实论述道:“亲属之间的藏匿犯人罪、隐灭证据罪,由来于自然的人情、友谊,被作为任意的免除刑罚事由。其根据在于缺乏期待可能性。所以,被减轻责任。”35国内著名刑法学者马克昌教授在《比较刑法学原理》一书中36亦指出:“这(即上述《日本刑法典》第105条——引者注)是基于东方道德期待不可能或期待困难在法律上的表现。”37
在中日刑法学者看来,大陆法系国家之所以规定亲属间的容隐行为具有法律所赋予的“免于处罚”或“可以免于处罚”的豁免权,是因为法律难以期待犯人亲属在可能的情况下不去帮助犯人逃避法律的惩罚,更难以期待犯人亲属能够主动控告或指证其罪行。38在此种“缺乏期待可能性”的情况下,如果法律仍强行规定犯人亲属不准包庇犯人、甚至规定他们有义务控告或指证其有罪亲属的话;那么,这样的法律本身就是在“强人所难”,其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由于直接违背人情、人性及刑法本身的“谦抑性”原则,这种法律规定势必强化“法律”与“人情”之间所本有的紧张关系,从而难以实现其预期效果,而且不利于培养公民愿意遵守甚至乐于遵守社会法律的良好风气。我们在此可以发现,“期待可能性理论”与西方古老法谚“法不强人所难”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有鉴于此,张明楷教授在《刑法格言的展开》一书中认为,期待可能性理论本身就是“法不强人所难”这一法律格言的理论化表述。39这就是西方亲属容隐制度在立法上获得确证的根据。有鉴于此,当前国内不少刑法学者强烈呼吁国家从“期待可能性理论”的角度修改刑法及刑事诉讼法中之相关条文,“将犯罪人的近亲属排除在伪证罪、窝藏包庇罪的犯罪主体之外”。40
其实,在国内哲学界关于儒家亲亲互隐问题的伦理争鸣中,不少学者均已有意或无意地从“期待可能性理论”的角度讨论了亲属容隐制的立法原理这一问题。其中,范忠信先生在《容隐制的本质与利弊:中外共同选择的意义》一文中就明确提到了“刑法学者所言[的]‘无期待之可能性’”41,并在其所展开的论述中反复强调法“不强人所难”42、不应“强人所难”43及“必不能强人所难”44的基本原则。然而,范先生这些十分有益的探讨在邓老师看来“都是隔靴搔痒”和“匪夷所思”的“天真”阐释。45如果邓老师认为范先生“不像一个严肃的法学家”的话,那么,让我们看看世所公认的法学权威、日本近代著名法学家松冈义正具体是如何论证亲属容隐制之立法原理的吧。
松冈义正在其经典著作《民事证据论》一书中讨论证人的作证义务问题时指出,所谓“证人之义务”,是指“凡负有证人义务者,须就受诉法院或受命推事受托推事讯问之事项,本其真实而为供述,此即所谓证人之义务也。”46松冈义正进一步指出:“对于证人应负证言义务之原则,亦于法律上有特别之规定者,有得拒绝证言之例外。”47而此处所谓的“有得拒绝证言之例外”的情况即包括亲属拒绝作证的权利。在解释这种亲属容隐权的原因时,松冈义正论述道:
“证人为原告或被告之亲属,或为原被告配偶者之亲属时,其所以得能拒绝证言者,诚以为证言之结果,不仅有害亲属间之和谐,而且如为不利亲属之证言,终为人情所不忍,强使为之,自有违反善良风俗及陈述不实之弊害,故法律承认有此关系之证人具有证言拒绝之权利。”48
在这里,松冈义正从“亲属间之和谐”、“人情所不忍”和“善良风俗”等角度对亲属容隐权之合理性的辩护与范忠信先生立足于“众情众心”、“民众淳厚”和“百姓亲法”等角度展开的分析在实质上并无二致。而这些因素恰恰全是邓老师所严厉批判的。那么,邓老师提出的批判理由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考察下这一问题。
在其行文中,邓老师先是全文照引了范忠信先生的如下文字:
“国家的长远利益是什么?国家的长久利益就在于民众淳厚、社会和谐、百姓亲法,如此才能达到长治久安。要达到这一目的,法律必须立于人情,必不能悖逆众情众心,必不能强人所难。”49
针对这段文字,邓老师提出了一连串的反诘:
“但是,一个放纵‘攘羊贼’、‘践踏司法尊严’甚至‘使杀人犯不受制裁’的国家,难道能够使‘民众淳厚、社会和谐、百姓亲法’吗?它立足于那些被偷、被杀者的‘人情’了吗?舜将杀了人的父亲‘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不正是自知自己的行为‘背逆众心’、不能见容于这个社会吗?如果他有理,干嘛要逃跑?”50
针对邓老师看似“有理”的反诘,我们可以提出如下几点商榷意见:
其一,舜之所以将杀了人的父亲“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其原因并不是舜“自知自己的行为‘背逆众心’、不能见容于这个社会”;真正“背逆众心”的人是舜的杀了人的父亲,而真正“不能见容于这个社会”的是舜父的杀人行为。
其二,舜要逃跑,也并不是因为舜本人的行为是“无理”的;相反,舜背着他父亲逃跑的行为当然是“有理”的。我们之所以长篇累牍地论证亲属容隐制的法律实质和法理依据,就是要证明舜的逃跑行为,即使是在今天,在奉行大陆法系的当代西方国家仍然是“合理合法”的正当行为。而舜的逃跑,真正目的是为了避开法律对其父亲的追究和审判。因为即使舜的藏匿行为是合法的,舜父杀人的行为却仍然是违法的,因此舜不能干涉法律对其父亲的惩罚,就像舜在放弃天子之位前不能阻止皋陶对其父亲的抓捕一样。此时我们可以模仿邓老师“如果他有理,干嘛要逃跑?”的口气问一句:“如果他不逃,他该如何保住父亲的命?”
其三,邓老师从“被偷、被杀者”的“人情”出发,驳斥范先生基于亲亲之情对亲属容隐制合法性之论证的做法同样值得商榷。一方面,“攘羊”、“杀人”等违法行为固然是罪恶的,且对受害者及其亲属造成了物质、人身或精神上的伤害,所以,从受害者及其亲属的“权利”、“人情”出发,依法惩办犯法者,是国家不容推迟的职责;另一方面,在捉拿、惩办犯法者的过程中,如果法律禁止犯人亲属藏匿犯人或帮助犯人逃跑,甚至强制犯人亲属控告或指证犯人的罪行,则法律必将伤及犯人亲属的“人情”,这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如此一来法律就陷入了两难境地,无论法律作何选择,都不能达到两全其美的效果。范忠信先生在其文本中丝毫没有否认这一情况,所以邓老师的两句简单的反诘并不足以摧毁范先生的论证。因为,法律在此具体情形中所面临的这一“二难选择”,是由法律本身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与道德相比,法的这种“特殊性质”表现为:法律是一套对人的“外在行为”具有或能够具有行之有效的约束的强制性规范。这里有两点值得强调:一,法律是对人的“外在行为”的规范,而且是一种“他律”性质的强制性规范;(所以)二,这种强制性规范本身对“行之有效”具有极高的要求。国内刑法学者张明楷教授曾谈到日本当代著名法学家团藤重光的如下看法:“康德曾就道德方面提出,‘因为你应当做,所以你能够做’(Du Kannst ,denn du sollst .)。就道德而言或许可以提出这种严格要求,但在法的世界,尤其是在刑法领域,只能说‘因为你能够做,所以你应当做’(Du sollst ,denn du kannst .)。由此看来,区分法律与道德是必要的。”51这里的“因为你能够做”一语本身就是从期待可能性的角度、从“不强人所难”的角度阐释立法的基本原理的。其实,康德本人在探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时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比如,在讨论“紧急避难权”的相关问题时,康德分析了“沉船争板”这一著名案例:“事实上没有任何刑法会对下述的这样一个人处以死刑:当一条船沉没了,他正在为了他的生命而推倒另一个人,使后者从木板上掉入水中,而他自己在木板上免于死亡。因为法律惩罚的威吓不可能比此时此刻害怕丧失生命的危险具有更大的力量。这样一条刑法,在此时完全失去了它所意图达到的效力。”52“沉船争板”是期待可能性理论中的著名案例。正如康德所分析的,我们之所以不能立法惩罚案例中那个推他人入水的人,是因为法律对处于此种情形下的个人是没有威慑力的;即使我们制定了更为严格的法律条文,我们也不能“期待”处于该紧急情况下的个体具有遵守这种条文的“可能性”。而对无期待可能性的行为人作出惩罚,显然有违法律本身的精神。这就是上文所引的松冈义正从“强使为之,自有……弊害”的角度、团藤重光从是否“能够做”的角度、康德从法律是否具有其“所意图达到的效力”之角度及范忠信先生从“多数人”是否能够做到的角度53所展开的理论分析的真实含义。所以,邓老师简单的一句反问——“它立足于那些被偷、被杀者的‘人情’了吗?”——看似有理有力,其实并没有触及范先生所讨论的整个问题的实质,更谈不上能够驳倒范先生的论证。
最后,针对范忠信先生的上述分析,邓老师以风趣的口吻总结道:“范先生说了一大通,什么伤感情啊,什么法律不能太严厉啊,什么执行难啊,都是隔靴搔痒。”54除了“隔靴搔痒”这一判决失之武断以外,邓老师的这个总结还是相当精妙的!简直和本文前面所引的松冈义正的论述如出一辙:要求亲属在法庭上互相指证,这种“伤感情”(“范先生”语)的行为确是“为人情所不忍”(松冈义正语);而且这种“太严厉的”(“范先生”语)法律“自有违反善良风俗……之弊害”(松冈义正语);所以这样的法律在实施过程中所必然遭遇的“执行难”(“范先生”语)的表现之一,正是“陈述不实”(松冈义正语)这一后果。
如果我们认为松冈义正的论述和“范先生”是一样的“天真”和“匪夷所思”,那么,我们就只能期待邓老师深入法学原理中就“现代西方容隐制”的“实质”作出更为“专业的”解释,从而也能将近百年来中日学者关于“容隐制”之立法原理的这场“半生不熟的讨论”真正“引向深入”,并最终针对“沉船争板”案例提出一个超越康德的法理解释。本文接下来还是回到预定的逻辑思路上,探讨现代西方亲属容隐制的人性论根基这一问题。
三、从“爱有差等”出发谈西方亲属容隐制的人性论根基
如果说基于期待可能性理论,法律只能立法赋予公民以亲属相隐的权利的话;那么我们接下来要问的是:是什么因素使得法律无法期待个体公民检举揭发其有罪亲属、甚至无法期待他们不去藏匿庇护其有罪亲属呢?答案很简单,就是上文所谈到的“人情”或“亲亲之情”。纵观围绕“亲亲互隐”所展开的两次大讨论,无论是刘清平,还是邓老师,都没有反对这一点。而在两次大讨论中主要引起争论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或如何评价这一“亲亲之情”。邓老师在其所发起的第一轮批判——即《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评郭齐勇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一文——中所转引的刘清平先生的原话,清楚地表明了论战双方的基本立场:
“依据上述规范(即刘清平先生所言及的‘包括英、法、德、美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的现行法律体系’中的亲属容隐条款——引者注),故意不告发等依然是违法犯罪行为,只是出于种种考虑‘不罚或减轻处罚’而已。这与孔孟儒家以及郭先生把父子互隐、窃负而逃当作‘直德’、‘天理人情之至’、圣贤典范行为加以推崇相比,显然有着本质的区别。”55
邓老师紧接着这段引文评论道:
“这里说得再清楚不过了。现代西方法律规定的容隐条款与中国古代容隐制度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不再是一个义务条款,而仅仅是一个权利条款。”56
这里首先有个表述上的问题值得分析:刘清平先生在此所谈论的“本质区别”明明是“西方国家的现行法律体系”中的容隐制度与“孔孟儒家以及郭先生的”亲亲相隐的道德观之间的“本质区别”;怎么邓老师就认定刘先生是在“清楚”地谈论“现代西方法律规定的容隐条款与中国古代容隐制度的根本区别”呢?邓老师在此后第二轮批判中指责陈乔见先生“把西方现代完备的容隐制度和容隐观念混为一谈”,并提醒说“容隐观念不等于容隐制度”,怎么在邓老师自己的分析中,就看不清“孔孟”及“郭先生”著作、文章中的容隐观与“中国古代容隐制度”的区别呢?
撇开这个表述上的问题,刘先生和邓老师的分析还是清楚地揭示了论战双方对容隐制之人性基础——即“亲亲之情”——的基本态度:以郭老师为代表的当代儒家学者主张把“亲亲相隐”视为道德上的善,即视为“直德”、“圣贤典范”以及“天理人情之至”;57而刘、邓二人则主张将之视为道德上的恶,视为“社会病毒”58、“滋生腐败”的“温床”59,因而是“狭隘”的、“陈旧”的以及“落后的”和“腐朽的”。60
在本文看来,刘清平先生和邓老师从“权利”和“义务”的角度,来区分西方现代法律规范中的容隐制与中国古代法律规范中的容隐制的做法是正确的;甚至他们从西方现代容隐制的“法定权利”出发批评甚至指责中国古代容隐制的“法定义务”的做法,也无可厚非。
但是第一,他们在论战中所进行的这一批评本身并无多大意义。因为包括郭老师在内的当代儒家学者所捍卫的,仅仅是“孔孟儒家传统”中的亲亲互隐理论,而不是中国古代法律传统中的亲属容隐制度。因此,以郭老师为代表的当代儒家学者从未提出要恢复或重建中国古代法律传统中的作为“法定的义务”的亲属容隐制的主张;恰恰相反,他们只是一直在呼吁我们的立法机关废除那些将亲属间相互揭发和指证罪行视为公民的法定义务的相关条文,从而将亲属容隐的权利以立法的形式还给国民。所以,当代儒家学者的这一立场与国内刑法学界的主流立场之间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主张与现代西方法律精神中的亲属容隐制也并无冲突。因此,邓老师通过批评中国古代法律规范中的亲属容隐制度来指责当代儒家学者的学术立场的做法,是不会取得他所希望的成效的。
第二,如果说刘清平先生和邓老师在上述引文中试图从西方法律中的亲属容隐“权利”出发,来批判郭老师等人从道德的立场对亲亲互隐所展开的辩护的话,那么他们的这种批判同样是无效的。西方现代法律确是把亲属容隐当作一项“法定的权利”来对待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只能从“权利”的角度来理解亲属容隐观,更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从道德的角度将“亲属容隐”及其背后的“亲亲之情”视为“直德”或“天理人情之至”。是谁规定我们不能从道德的角度赞许某项“法定的权利”的?仅仅因为亲属容隐在西方是一项法定权利,就意味着“孔孟儒家以及郭先生”等从道德的角度赞许亲属容隐及“亲亲之情”的做法是错误的吗?显然,无论是刘清平先生还是邓老师都不能给出让人满意的回答,因为他们的这种批评本身就是一种错位的批评,即用西方法律层面中的是非标准来衡断儒家道德领域中之观点的是非对错,而这在根本上是混淆道德与法律两个不同范畴的做法。即使刘先生或邓老师把西方文化视为一种“普世价值”,并打算以这种“普世”标准来评判中国传统,他们也应该从西方文化在道德层面上对亲属容隐的人性论根基所作的解析出发,来反观中国儒家传统关于亲亲相隐的道德态度是否合理,因为只有这样的比较才是同一层面的比较,且只有这样的比较才有真正的“可比性”。本文接下来就从这一角度察看西方亲属容隐制度的道德基础或曰人性论根基这一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其实邓老师本人已在无意之中作了某种有益的探讨了。比如,在解释本文第一部分所引的孟德斯鸠的两段文字中“妻子怎能告发他的丈夫呢?儿子怎能告发他的父亲呢?”一句的含义时,邓老师指出:“这里的‘怎能’……是‘情何以堪’、‘怎么能忍心’的意思。”61解释的好!但本文所要指出的是,如果沿着这一解释思路继续走下去,邓老师本人对孟德斯鸠这两段文字的总体理解将会受到颠覆。因为,“情何以堪”和“怎么能忍心”的解释本身就意味着,在孟德斯鸠看来,亲属相互告发的行为是为人“情”、人“心”所不“堪”和不“忍”的行为。所以,英国学者Thomas Nugent即直接将这两句话译为:“Thiswas contrary to nature: a wife to inform against her husband! a son to accusehis father!”62这里的意思再清楚不过,即在Nugent看来,孟德斯鸠所要表述的是妻子控告丈夫与儿子控告父亲的行为本身就是违背人的自然天性的行为。严复在翻译此段文字时亦指出:“而妻子证其夫、父则逆天矣。”63
既然亲属相互告发的行为本身有违人的天性和道德良心,那么,孟德斯鸠在这里所反对的就不仅仅是勃艮第王贡德鲍强制亲属相互告发的规定了,他在此甚至不同意亲属相互告发这一违背人性的行为本身。对前者的反对(贡德鲍的规定),意味着孟德斯鸠将亲属容隐视作了人的权利;而对后者的反对,意味着孟德斯鸠同时将亲属容隐视作了人的义务。这就是孟德斯鸠将亲属相互告发视为比偷窃“更为罪恶的行为”的原因,也是孟德斯鸠反对列赛逊突斯准许亲属相互告发之法律的原因。由此可见,邓老师单单从“家庭成员有按照亲属关系相隐的权利”的角度来理解孟德斯鸠的本意,反对我们从“义务”的角度将“怎能”理解为“怎么允许”的做法就相当不妥了。64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邓老师一再错误地认为孟德斯鸠的观点与“家庭成员按照法律关系揭发亲属罪行的权利”是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的。65
按照邓老师一贯的行文逻辑,他大概会质问我们或孟德斯鸠:贡德鲍强制亲属相告的规定固然是违反人性的,因为它否定了亲属相隐的权利;但是,准许亲属相告的列赛逊突斯的法律怎么也是违反人性的呢?你们是否考虑到受害者的“人性”了呢?其实,孟德斯鸠的论述再清楚不过:一方面,正是由于考虑到了受害者的人性,法律才必然要去制止偷盗和通奸行为,孟德斯鸠在讨论基于人的本性(或自然)的法律时即指出:“一个‘智能存在物’损害了另一个‘智能存在物’就应当受到同样的损害。”66但另一方面,因为亲属相告的行为本身也是违反人性(或自然)的,所以,法律就不能为了惩罚偷盗和通奸,而准许甚至强制亲属相告。有基于此,孟德斯鸠才批评贡德鲍的法律“为了要对一种罪恶的行为进行报复,……竟然规定出[另]一种更为罪恶的行为。”67
从现代西方亲属容隐制的内容来看,孟德斯鸠取消亲属相告的权利、将亲属相隐视为法定义务的做法,或许是值得商榷的。但是,孟德斯鸠从人的自然天性的角度,论证亲属相隐背后的道德原理的做法,恰恰成为了现代西方亲属容隐制的人性论根基。这里的逻辑并不复杂:由于相互间的“自然感情”,68我们在告发亲人的罪行时,总是感觉到一种道德上的困难和阻力——即邓老师所说的“情何以堪”、“怎么能忍心”——,这种困难和阻力使得法律对亲属相告行为缺乏合理的期待可能性;因此法律只能容许亲属相隐的行为,并赋予其免于处罚的法律豁免权。这一推理和另一位近代启蒙思想家霍布斯的论述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霍布斯在讨论相关问题时指出:“控告父亲、妻子或恩人等使之判刑后本人会陷入痛苦之境时,情形也是这样。因为这种控告者的证据,如果不是自愿提供的,在本质上就应当认为是不可靠的,因而也就是不足为据的;而当一个人的证据不可信时,他就没有义务提供。”69
其实,从人性的角度强调并尊重人与人之间的亲亲之情,是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的常见做法。如休谟在谈论“对于亲友的爱”时指出:“血统关系在亲、子之爱方面产生了心灵所能发生的最强的联系。”70休谟进而论述道,基于对亲友的自然的“爱和好感”,在我们拿他们与“陌生人比较的时候,我们总不免要偏袒”我们的亲友。71
此外,休谟在讨论“同情”概念时指出,基于“同情”,我们对于陌生人也具有一种爱和好感。为了论证这一观点,休谟列举了一个和孟子“孺子入井”类似的例子:“假使我看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睡在田间,有被奔马践踏的危险,我就会立刻去援救他。”72只是在休谟看来,我们内心对他人的那种天然的和自发的同情心,在强度上不及我们对自己亲友的爱罢了。例如他说:“[血统]关系减弱,这种情感的程度也就减弱。”73为了阐述这种类似“爱有差等”的自然同情心,休谟甚至说:“人类的慷慨是很有限的,很少超出他们的朋友和家庭以外,最多也超不出本国以外。”74因此,休谟将人性中的这种对他人的“同情心”称为“有限的同情心”。
那么,人性中的这种“有限的同情心”,即对亲友和对他人有所不同的“差等之爱”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吗?当然不是。在休谟看来,我们的道德原则,恰恰就是从这种“有限的同情心”中推导出来的。他甚至说:“一个人如果……不顾他的家人,而在利害冲突之际,偏向了陌生人或偶然的相识,我们就要责备他。”75休谟的这一论述表明:“爱有差等”,不仅是人性中天然的道德情感,76而且也是我们日常行为中的一项道德义务。在我们违背这一义务时,我们就会受到他人基于道德良心的“责备”。
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也表达了与休谟类似的观点。比如他在讨论“按约建立的国家和主权的继承问题”时指出,如果国家的统治者——君主在位时没有立下指定继承人的遗嘱,且又没有先例和习惯可依的话,我们就应当认为君主“本人的子女应优先任何其他人继位”;而在君主“没有子嗣时,兄弟应先于外人,这样推下去,总是血缘较近的人先于较远的人”。这么做的原因是,基于我们的“天性”,“我们永远可以认为亲属愈近、感情也愈厚”。77
在这里,本文当然不是要为霍布斯政治哲学中关于君主继承权问题的理论做辩护。本文只是通过上述的分析指出:在霍布斯、休谟和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们那里,“自由”和“平等”虽然是他们的政治哲学和法律思想所坚持的核心理念,但是,他们对“平等”的理解,绝不是抽离了亲情之后的那种毫无差别的“绝对平等观”。相反,他们总是在“爱有差等”的框架下理解人性和道德,强调并论证了个体对亲属所负有的某些道德义务在顺序上优先于陌生人。基于这种优先性,他们认为,在亲属与他人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个体在道德上具有优先保护其亲属的义务,在此基础上,霍布斯和孟德斯鸠呼吁维护平等和正义的法律本身能够充分尊重和维护这一道德要求。这就是亲属容隐由道德的义务进至法定的权利的逻辑过程。
至此我们就充分证明了郭老师关于“‘亲亲相隐’既是义务,又是权利”的论述。78说“亲亲相隐”是义务,是就道德和人性的层面上而言的;说“亲亲相隐”是权利,是就法律和制度的层面上而言的。因此,以郭老师为代表的当代儒家学者一方面将“亲亲相隐”视为“直德”另一方面呼唤当今国民的法定隐亲权的做法,从西方现代亲属容隐制的立法原理及人性论根基的角度而言,不仅是毫无矛盾的,而且是合情合理的。《也谈“子为父隐”与孟子论舜——兼与刘清平先生商榷》是“亲亲互隐”论战爆发以来郭老师所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批驳性文章,该文开篇即强调指出,我们要从“法律”和“深度伦理学”两个不同的层面来理解儒家经典关于“亲亲互隐”的相关论述,79这与郭老师在其迄今为止所公开发表的的最后一篇批驳性文章“《< 儒家伦理新批判>之批判》序言”中再次呼吁我们从道德义务和法定权利的双重角度来还原儒家“亲亲互隐”命题所包含的多层次的丰富的内涵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80
由此反观围绕“亲亲互隐”问题所展开的两次大讨论,我们可以发现,刘清平从“法定权利”的角度批判儒家从“道德义务”的层面对“亲亲互隐”所作的相关阐述,从根本上就是一种错位的批判,刘先生在其文章中丝毫没有意识到法律与道德两个层面或范畴之间的真正区别,他望文生义地理解范忠信先生基于“期待可能性理论”对亲属容隐制的立法依据所做的有益探讨,并武断地认为范先生的解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荒唐理由”,81所以刘先生在其单向度的理论视野中动辄得出“儒家伦理的深度悖论”这一谬见是丝毫都不值得奇怪的;82与刘先生相比,邓老师力图从西方文化中所包含的“普世价值”出发,展开其对儒家伦理的批评,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一批评自然比刘清平先生更进了一步。但是,当邓老师立足于所谓西方所发现的“普世价值的真正基础和根源,即普遍理性以及人人具有的平等的人格”这一前提,来指责中国儒家传统根植于“爱有差等”、“(人)格有差等”的“亲亲互隐”观念时,83他恰恰没有意识到,他所谓的“人人平等”这一西方普世价值的基础,并不是现代西方亲属容隐制的“真正基础”;因此,当邓老师想当然地认为西方现代亲属容隐制所保护的是“人人平等的权利”或“个人权利(隐私权)”时,84启蒙思想家们如孟德斯鸠和霍布斯等人,却是从“爱有差等”这一人的“自然”或“天性”的角度,确立亲属容隐权之道德根基的。85由此看来,西方现代容隐观和容隐制,与儒家传统的容隐观之间所具有的,并不是邓老师所谓的“本质区别”,而恰恰是某种“本质上的一致性”。86在此基础上,邓老师所谈论的“新儒家的误区”87、以及所谓“儒家伦理结构中的根本性矛盾”88等断语,都是值得重新商榷和批判的。
四、结论
在《儒家伦理新批判》一书的序言及该书的封底中,邓老师强调,其对儒家伦理的批判,不是“笼统”地立足于中西文化“各种观点和口号的比较”,而是立足于两大文化体系的“文化模式”和“逻辑构成”的基础之上的。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日益加深的当代,邓老师的这一提法本身无疑是新颖而独到的。但是,在本文看来,邓老师围绕《儒家伦理新批判》一书的主题“亲亲相隐”来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批判时,他对西方现代亲属容隐制的理解远远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和根本。正如本文前三个部分所揭示的:他从“隐私权”的角度对西方容隐制的法律内涵所作的界定是不恰当的;他就西方容隐制的法理依据问题所做的相关探讨及对范忠信先生所作的相关批评是错误的;而这种种不当和错误,均是建立在他对孟德斯鸠案例的误读、对西方现代亲属容隐制的人性论根基的忽视的基础之上的。一直以来,邓老师都是令本人甚为敬重的学界前辈,本人在此发文和邓老师商讨并向其请教相关问题,仅仅是希望能够将儒家“亲亲互隐”观的批评者对所谓“西方现代亲属容隐制”的理解真正导向深入罢了,我相信这也是邓老师所乐意看到的。